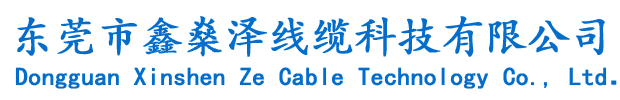房改房在繼承案件中的司法認(rèn)定
房改房是國家房改政策的產(chǎn)物。房改政策關(guān)懷的對(duì)象是以家庭而非個(gè)人為基礎(chǔ)的,其厚意公平地指向作為購房主體的夫婦雙方(哪怕是已故的)并惠及他們的合法繼承人。
【案情簡介】
本案中被告趙某與被繼承人王某原系夫妻關(guān)系,后被繼承人王某因病去世,此后王某和被告共同購買的房改房發(fā)生繼承。第一原告趙某某系被告與被繼承人王某的婚生子,第二原告系王某的母親,王某父親于2012年去世,第三原告系被繼承人弟弟。1998年12月16日王某去世。在王某去世前曾與被告共同購買了單位的公產(chǎn)房,即朝陽區(qū)某小區(qū)36號(hào)樓502室。后被告將此房交回原單位,置換成另一小區(qū)1001室及1004室兩套房屋,面積共112.53平方米。三原告依照法定繼承應(yīng)得面積為37.5%份額,折合成折價(jià)款約207萬元。按照上述要求三原告向法院提起訴訟。
審理中,被告稱在王某去世前,夫妻二人僅用共同財(cái)產(chǎn)26618.68元支付了502室的第一筆購房款,只承認(rèn)502第一筆購房款的一半屬于王某的遺產(chǎn)。后來置換的1001和1004號(hào)房屋是由于被告職務(wù)、身份的變化才能購買的,認(rèn)為這兩套房屋與王某無關(guān),不同意三原告繼承該房屋,僅愿意支付一定的遺產(chǎn)使用費(fèi)。
【一審判決】
一審法院審理后認(rèn)為雖然在王某去世后,趙某就502號(hào)房屋簽訂的《房屋買賣契約》,交納了第二筆購房款并取得所有權(quán)證書,但王某生前一直與被告共同租住在502號(hào)房屋內(nèi),且有購買的意思表示,并于1998年12月7日交納了部分購房款,購房時(shí)也使用了王某的工齡。所以認(rèn)定該房屋屬于王某與被告的夫妻共同財(cái)產(chǎn)。王某去世后,被告未經(jīng)其他繼承人同意,將502房屋上交原單位,另行購買了1001和1004房屋,故,502房屋中原屬王某的一半財(cái)產(chǎn)轉(zhuǎn)化為1001和清房屋中的相應(yīng)財(cái)產(chǎn)份額,該部分財(cái)產(chǎn)屬于王某的遺產(chǎn),應(yīng)依法發(fā)生繼承。但一審法院并未考慮房改房的特殊屬性,未采納我方提出的關(guān)于房改房優(yōu)惠政策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僅根據(jù)繼承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按照三原告的各自法定繼承比例作出了判決,判決被告給付三原告折價(jià)款共計(jì)約143萬元。
【二審情況簡介】
三原告及被告均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第一中級(jí)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原審原告認(rèn)為趙某獲得1001和1004房屋時(shí),仍是以趙某和王某二人名義申請(qǐng)、登記并使用了王某的工齡等福利待遇,仍是共同購買,且國家政策也有規(guī)定。1001和1004房屋是502房屋的購買公有住房權(quán)利的轉(zhuǎn)換,所以請(qǐng)求認(rèn)定1001和1004房屋總面積的一般為王某所留遺產(chǎn),并以此分割。原審被告認(rèn)為不能認(rèn)定502房屋為夫妻共同財(cái)產(chǎn),且502與1001和1004房屋沒有直接聯(lián)系,王某留有的遺產(chǎn)僅為13309.34元,應(yīng)按照該款額計(jì)算在全部購房款中的比例。
【律師評(píng)析】
一、原審判決在關(guān)于朝陽區(qū)關(guān)東店北街22號(hào)樓1001號(hào)和1004號(hào)房屋是否屬于王某與趙某夫妻共同財(cái)產(chǎn)的問題上,事實(shí)認(rèn)定錯(cuò)誤,適用法律錯(cuò)誤。
原審判決書稱“王某去世后,趙某因工作職務(wù)、級(jí)別的調(diào)整而有資格并購買了1001號(hào)及1004號(hào)房屋,亦補(bǔ)交了購房款,而且趙某再婚后另外補(bǔ)交了一筆房屋超標(biāo)款,故三原告關(guān)于1001號(hào)及1004號(hào)房屋屬王某與趙某的夫妻共同財(cái)產(chǎn)之抗辯,沒有依據(jù),本院不予采信。”對(duì)此上訴人均不能同意。我們的依據(jù),除了經(jīng)質(zhì)證認(rèn)定的事實(shí)——即趙某獲得1001號(hào)和1004號(hào)房屋時(shí),仍是以他和王某二人名義申請(qǐng)、登記并使用了王某的工齡等福利待遇,仍是共同購買——之外,還有國家房改政策,以及政策解釋性文件。
國家房改政策規(guī)定,職工按成本價(jià)購買公有住房,每個(gè)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趙某與王某購得502房屋后,他從此永遠(yuǎn)喪失了再次與王某的名義一起以成本價(jià)另行新購單位公有住房的可能。換言之,2001年,遺產(chǎn)未分割且處于喪偶未再婚(而非未婚或再婚)狀態(tài)的趙某,因個(gè)人工作職級(jí)的調(diào)整有資格得到的只是住房調(diào)整的“機(jī)會(huì)”(這機(jī)會(huì)必然也必須沿用與王某的共同名義及優(yōu)惠政策才得以落實(shí)),絕無資格再次新購單位的成本價(jià)住房——無論以他自己的名義還是以和王某一起的名義,否則有違國家房改政策。
因而,趙某取得1001號(hào)和1004號(hào)房屋,是原有502號(hào)房屋的購買公有住房權(quán)利的轉(zhuǎn)換。另外,單位將502房已繳納的購房款直接折抵成1001號(hào)和1004號(hào)房屋的購房款這一情況,也可說明這一問題。故而,關(guān)東店二房的獲得,名為“購買”,實(shí)則僅僅是對(duì)原有住房狀況的一次“調(diào)整”而已,其結(jié)果是以1001號(hào)和1004號(hào)房屋對(duì)先前的502號(hào)房屋進(jìn)行替換,但趙某、王某二人的所有權(quán)及權(quán)屬關(guān)系并未因房屋形態(tài)的變遷而改變或喪失,而是隨之動(dòng)態(tài)地轉(zhuǎn)移到因調(diào)換而得來的1001和1004號(hào)房屋上,且王某的遺產(chǎn)既然先前未曾分割,那么,此二房就仍為夫妻共同共有。至于趙某“補(bǔ)”交了房款和超標(biāo)款,并不影響共同共有的性質(zhì)。
說白了,就權(quán)屬上而言,關(guān)東店二房實(shí)際上還是502號(hào)房。既然502號(hào)房是夫妻共同財(cái)產(chǎn),那么在本案的情況下,關(guān)東店二房必須且必然也是夫妻共同財(cái)產(chǎn)。因而,也就和“公民死亡時(shí)遺留的個(gè)人合法財(cái)產(chǎn)”等法律原則其實(shí)并不抵觸。遺產(chǎn)包括死者遺留下來的財(cái)產(chǎn)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本案中表現(xiàn)為房屋形態(tài)的關(guān)東店二房,雖然得自王某身后,但承繼于被繼承人與趙某共同共有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來自王某生前,所以即使王某生前沒有實(shí)際占有該房產(chǎn),也應(yīng)視為夫妻在婚姻關(guān)系存續(xù)期間所得財(cái)產(chǎn)而在繼承時(shí)納入遺產(chǎn)的范圍。
二、一審判決適用法律依據(jù)錯(cuò)誤,導(dǎo)致三上訴人在遺產(chǎn)的可繼承范圍上存在嚴(yán)重錯(cuò)誤,因而對(duì)各繼承人應(yīng)當(dāng)繼承的房屋折價(jià)款的數(shù)目存在錯(cuò)誤。
《民法通則》規(guī)定:民事活動(dòng)必須遵守法律,法律沒有規(guī)定的,應(yīng)當(dāng)遵守國家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釋[2013]7號(hào)文件以“與現(xiàn)行房改政策不一致”為由廢止了[2000]法民字4號(hào)司法解釋性文件,也足見裁判此類糾紛時(shí)法律應(yīng)該適應(yīng)政策,所以針對(duì)本案而言法院更應(yīng)該根據(jù)國家現(xiàn)行房改政策的有關(guān)規(guī)定作出判決。
房改房是國家房改政策的產(chǎn)物。房改政策關(guān)懷的對(duì)象是以家庭而非個(gè)人為基礎(chǔ)的,其厚意公平地指向作為購房主體的夫婦雙方(哪怕是已故的)并惠及他們的合法繼承人。
房改房是國家房改政策的產(chǎn)物,原審法院判斷房改房權(quán)屬卻規(guī)避房改政策,不顧先后兩處房產(chǎn)之間特殊、深刻的邏輯關(guān)系,斷章取義地看待關(guān)東店二房并削足適履地生硬套用繼承法認(rèn)定其權(quán)屬關(guān)系,這既不正確,也不公平,實(shí)際上是對(duì)王某以及除趙某外的其他繼承人合法權(quán)利的削奪。
【二審判決】
二審法院在審理中采納了原審原告代理律師的意見,認(rèn)為一審法院在對(duì)房屋共同份額及折價(jià)款數(shù)額的確認(rèn)使用法律不當(dāng),依法作出了改判,最終判決原審被告趙某向原審三原告共計(jì)支付折價(jià)款約206萬元,幾乎全部支持了三原告的訴訟請(qǐng)求。
(來源:互聯(lián)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