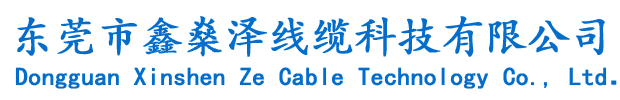,
我國物權請求權制度的解釋論
【摘要】我國《物權法》確立的物權請求權類型包括:原物返還請求權、排除妨害請求權和消除危險請求權,不包括恢復原狀請求權。物權請求權制度不僅強化了物權的保護,而且厘清了侵權責任和物權請求權的關系。該制度可以準用于準物權,可以類推適用于人格權,但不能類推適用于債權。各種物權請求權應作細化的分析。《民法通則》第135條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不應適用于物權請求權。物權請求權行使的費用原則上由物權人負擔,相對人有過錯時,則由相對人負擔。
【關鍵詞】物權請求權;原物返還請求權;排除妨害請求權;消除危險請求權
【全文】
一、我國物權請求權制度的確立及其意義
物權請求權,是指為了恢復物權的圓滿狀態或者防止妨害的發生,物權人請求義務人為一定行為或者不為一定行為的權利。[1]
學界一般認為,我國《物權法》確立的物權請求權類型包括:原物返還請求權、排除妨害請求權和消除危險請求權。不過,《物權法》上還規定了恢復原狀請求權,衡量法條的位置,立法者似乎要將其作為物權請求權的具體類型。[2]筆者認為,恢復原狀請求權不屬于對物權請求權的規定,而屬于侵權損害賠償的范疇,理由在于:第一,物權請求權屬于直接打擊侵害的物權保護方法,而侵權損害賠償屬于間接填補損害的物權保護方法。[3]恢復原狀顯然是要填補損害,而非直接打擊侵害。第二,物權請求權的行使不以損害的實際發生為要件,而侵權損害賠償則必須以損害的實際發生為要件,正所謂“無損害即無賠償”。而恢復原狀必然以損害已經發生為前提。第三,物權請求權的行使不以相對人擁有責任財產為前提,而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應當以賠償義務人擁有責任財產為前提。恢復原狀義務的承擔應當以義務人擁有責任財產為前提,例如,義務人要更換,必須要擁有責任財產。
物權請求權制度是大陸法系國家的重要制度,其創設的目的是為了強化對物權的保護。羅馬法及法國民法訴訟法上有關保護所有權的各種訴權,實際上就已形成了物權請求權的基本內容。不過,該制度最早明確規定于《德國民法典》,并被后世大陸法系很多國家所效仿。[4]我國正是借鑒了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經驗,于《物權法》中第一次確立了物權請求權制度。該制度的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具體表現為:其一,強化了物權的保護。既有的法律僅僅規定了侵害物權的侵權責任,而物權請求權的行使不僅不要求加害人的過錯,也不要求損害的發生,因此,強化了對物權的保護。其二,厘清了侵權責任和物權請求權的關系。我國《民法通則》第134條規定的侵權責任形式范圍廣泛,包括了返還原物、排除妨害、消除危險等。這就混淆了侵權責任與物權請求權。《物權法》第34、35條的規定實際上結束了這一混亂局面,并使得《民法通則》第134條的規定部分地被凍結。其三,形成了實質意義上的絕對權請求權制度。雖然我國知識產權法上確立了侵害知識產權的“禁令”制度,但是,該制度原本屬于英美法系,與我國大陸法系的概念規則體系多有抵觸。《物權法》上物權請求權制度的確立表明我國回歸大陸法系,并通過該制度類推適用于人格權等絕對權,從而形成了實質意義上的絕對權請求權制度。其四,明確了違法性要件的獨立地位。物權請求權的行使雖不要求過錯,但以違法性為其要件。該制度的確立突顯了違法性要件的價值,并可能影響到侵權法領域違法性要件的獨立。
二、物權請求權制度的適用范圍
我國《物權法》在總則部分規定了物權請求權,這意味著,物權請求權制度可以適用于所有的物權。不過,是否所有的物權人都可以行使該項權利?對此,學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只要物權請求權的行使與物權的性質不相違背,物權人就可以行使該項權利。此外,就物權請求權的適用范圍而言,還有如下問題值得探討:
其一,物權請求權的是否適用于準物權?準物權的范圍比較廣泛,我國《物權法》僅規定了部分準物權,如海域使用權等。筆者認為,準物權的性質而言決定了,其只能是準用物權制度,因此,只有在不與準物權的性質相違背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物權請求權。
其二,物權請求權是否可以適用于人格權?人格權與物權一樣都屬于絕對權,理論上一般認為,人格權主體應當享有人格權請求權,以強化對人格權的保護。可惜的是,我國現行法尚未確認人格權請求權。筆者認為,《物權法》關于物權請求權的規定可以類推適用于人格權,這符合“類似情況類似處理”的法律原則。
其三,物權請求權是否可以適用于債權?對此,學界存在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一是肯定說。此種觀點認為,物權請求權可以適用于債權,只要有妨害,就可請求排除,不考慮是物權還是債權。二是否定說。此種觀點認為,債權人僅能請求債務人行為,對第三人不得請求給付,因此,無法行使物權請求權。[5]筆者認為,物權請求權不能適用于債權,因為債權不具有社會典型公開性,其存在一般不為第三人所知悉,如果將物權請求權適用于債權,將不適當地限制了人們的行為自由。因此,《物權法》的相關規定不能類推適用于債權。
三、原物返還請求權
原物返還請求權,是指不動產或者動產被無權占有時,權利人享有的請求占有人返還原物的權利。[6]
(一)原物返還請求權的構成要件和效力
原物返還請求權的行使,必須滿足如下要件:
其一,相對人是現在占有該物的人。占有人必須是現在占有物的人,即在提出請求時仍然占有物的人。如果曾經的占有人現在已經不再占有該物,或者物已經滅失,就不應再請求其返還原物,他也無法返還。現在占有人可以是直接占有人,也可以是間接占有人。[7]間接占有人可以返還原物,也可以讓與其對直接占有人的請求權。
其二,相對人的占有構成無權占有。所謂無權占有,是指被請求時已無占有的本權。[8]換言之,占有本身具有違法性。至于占有人是否具有過錯、占有人是否善意、占有人是自始無本權還是嗣后無本權、占有人如何獲得占有(如搶奪、盜竊、拾得等),都不影響該權利的行使。[9]尤其是,原物返還請求權的行使并不以相對人具有過錯為前提,這體現出物權請求權不具有道德譴責的色彩。考慮到舉證責任分擔的一般原理,“無權占有”是消極事實,原告不負舉證責任。如果被告抗辯其為有權占有,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10]
問題在于,相對人是否必須具有責任能力?筆者認為,在理論上,責任能力是判斷過錯的前提,既然相對人是否具有過錯是不必要的,因此,相對人也就不必具有責任能力。
其三,請求權的主體必須是所有人和他物權人。這里所說的所有人既可以是單獨的所有人,也可以是共有人,[11]還包括處于類似于所有人地位的人,例如,破產管理人。我國的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也可以行使該項權利。
值得探討的是,他物權人是否可以行使該項權利?從一些國家的立法來看,原物返還請求權應當是所有人或者與所有人地位類似者的權利,但是,我國物權法是否應當作出此種限制?筆者認為,我國《物權法》第34條使用了“權利人”的表述,似乎請求權的主體可以包括所有的物權人。另外,他物權人是否享有原物返還請求權還必須考慮債權人代位權制度的設計,在我國合同法上,債權人代位權的客體不包括物權請求權,所以,他物權人就應當享有原物返還請求權,以避免所有人不行使該項權利而使他物權人遭受損害。
(二)原物返還請求權中的若干疑難問題
1.原物返還請求權是否適用于貨幣?
貨幣系具有高度替代性的物。法諺有“貨幣屬于其占有者”。因為貨幣的本質就在于流通,而且在流通過程中,完全漠視其個性,因此,除了現實支配(占有)之外,還認可法律上的可能支配(所有權),這就不太合適。[12]問題是,原物返還請求權是否可以適用于貨幣?筆者認為,既然貨幣適用“占有推定為所有”的規則,原則上應當不適用。但是,如果原貨幣所有人可以明確確定具體的貨幣(如記住了貨幣上的號碼),此時也應當允許其請求原物返還。
2.在遺失物被無權處分時,物的所有人向買受人請求原物返還,是否屬于物權請求權制度中的原物返還請求權?
筆者認為,既然《物權法》第107條確立了遺失物原則上不能善意取得的規則,那么,遺失物的處分并不導致所有人喪失其所有權,因此,其請求返還原物的權利應當是物權請求權之中的原物返還請求權。只不過,該法第107條的規定應當屬于原物返還請求權的特殊規定,該條中的權利要受到2年的訴訟時效的限制。
3.違章建筑的建造人是否享有原物返還請求權?
所謂違章建筑,是指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或者未按照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規定建造的建筑物和工作物。[13]建造人是否享有原物返還請求權,取決于其是否享有所有權。對此,我國學界看法不一。有學者認為,建造人僅享有占有權;也有學者認為,建造人享有所有權。筆者認為,建造人對其違章建筑也享有所有權,只是因為其建造行為不合法,其無法辦理登記,因此,他處分該建筑的行為不產生物權效力。綜上,違章建筑的建造人也享有原物返還請求權。
4.所有人將其物設定了用益物權、租賃權等,第三人侵奪了占有,所有人是否可以向第三人請求原物返還請求權?
對此,存在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所有人應當可以行使該項權利,因為他仍然是所有人。另一種觀點認為,所有人不得請求向自己返還,只可以請求向用益物權人或租賃權人等返還,否則,就會導致所有人侵奪他物權人的占有。[14]筆者認為,后一種觀點值得贊同,如此既可以維護所有權人的利益,又可以避免他物權人或債權人(如承租人)遭受損失。
四、排除妨害請求權
排除妨害請求權,相當于國外法上的妨害停止請求權,是指物權因侵奪占有以外方式被妨害時,權利人享有的請求排除妨害的權利。
(一)排除妨害請求權的構成要件和效力
排除妨害請求權的構成要件包括:
其一,相對人以侵奪占有以外的方式妨害物權。所謂妨害,是指以侵奪占有以外的方式,影響了物權的圓滿狀態。[15]《物權法》有意使用了“妨害”的概念,從而力圖區分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中的“侵害”和物權請求權構成要件中的“妨害”。筆者認為,“妨害”與“侵害”的區分實際上很困難,我們應當將其與“損害”聯系起來理解,在妨害的情況下,并以造成損害為前提,而僅僅強調物權的圓滿狀態受到影響。
妨害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事實上的妨害,如甲的松樹被風吹折,倒入乙的庭院,妨害乙所有權的行使;二是法律上的妨害,如甲將乙的房屋登記為自己所有,因登記有公信力,可能導致乙喪失所有權。這兩種妨害都可以請求排除。[16]妨害必須是仍然在繼續的,如果妨害已經結束,就沒有請求排除的必要。至于妨害是因何種原因而產生的、相對人是否具有過錯等,都不影響排除妨害請求權的行使。只要對于妨害的事實享有將其排除的支配力,該人就是相對人。[17]
其二,妨害構成違法。在理論上,排除妨害是否必須以違法性為要件,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多數學者認為,妨害必須具有違法性;少數學者認為,違法性要件是多余的,可以被容忍義務是否存在代替。[18]筆者贊同多數學者的看法,因為容忍義務的存在僅僅表明該妨害并不構成違法。例如,根據相鄰關系規則,受害人應當容忍對方的排放炊煙的行為,此時,就不能認定違法性的存在。
另外,我國《物權法》第35條并沒有明確妨害是否必須違法,但是,從解釋論的角度來看,我們應當認定違法性要件的存在,理由在于:(1)從權利不可侵害性來考慮,既然物受到妨害,就已經構成了違法。(2)從平衡物權人的權利與社會一般人的行為自由考慮,也應當要求違法性要件。如果物權人對于其應當容忍的輕微妨害也可以主張排除妨害,則社會一般人的行為自由不復存在。(3)從比較法的角度考慮,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和理論都承認違法性要件,我國既然借鑒了國外的制度,也應作同樣理解。
其三,請求權主體是物權人。我國《物權法》在總則部分規定了排除妨害請求權,這就意味著該權利可以為所有物權人行使,包括所有權人和他物權人。
如果滿足了上述要件,物權人就可以請求相對人排除妨害,回復物權的圓滿狀態。這里所說的“妨害人”包括行為妨害人和狀態妨害人,前者是以自己的作為或者不作為造成了妨害的人,后者是對物上的妨害要負責任的人,比如,即使妨害是由于自然原因形成的,妨害人也要承擔責任。[19]
(二)排除妨害請求權的若干疑難問題
1.違法性的判斷
在排除妨害請求權構成要件中,妨害的違法性應當如何認定?對此,學界鮮有論及。在侵權責任法之中,違法性的認定理論有三種:(1)結果不法說(Erfolgsunrecht)。此種觀點認為,在侵害權益時,不需要對違法性進行驗證。權益侵害本身就征引了違法性,[20]加害人應當證明違法阻卻事由的存在。[21](2)行為不法說(Handlungsunrecht)。此種觀點認為,在故意侵權的情況下,違法性仍然通過權益侵害來征引。[22]而對于過失侵權行為,只有行為人違反了一個具體的法律上的行為規則,或者違反了一般的注意義務,才應當認定其行為的違法性。[23](3)折衷說。此種觀點認為,在直接侵權的情況下,要依結果不法說來認定違法性。[24]而對于不作為侵權和間接侵權,要依據行為不法說來判斷其違法性。[25]
妨害的違法性的認定,也應當適用侵權法上違法性理論。問題在于,行使排除妨害請求權時,究竟適用何種違法性認定理論?筆者認為,考慮到排除妨害請求權的行使并不以相對人的過錯為要件,因此,應當采結果不法說。如果采行為不法說,就要求相對人沒有違反注意義務,從而導致實質上要求相對人具有過錯。
2.“妨害”的認定是否應考慮特定區域的習俗?
物權的圓滿狀態受到影響,就認定妨害的存在。問題在于,妨害的認定是否考慮到特定區域的習俗?舉例而言,在一些農村地區,人們大多認為,廁所門正對著鄰居家客廳,是不吉利的;在鄰居的家門前修建化糞池,會給鄰居帶來不幸等。“受害人”是否可以基于其物權行使排除妨害請求權呢?筆者認為,“妨害”的認定應當考慮特定區域的習俗。如果根據特定區域的習俗可以認定為妨害,就應當允許受害人行使排除妨害請求權,如改變廁所門的方向等。當然,法官考慮的習俗必須不能違反強行法的規定和法律基本原則。
3.“妨害”是否僅限于物權的圓滿狀態受到影響,是否還包括物權人受到了影響?
理論上一般認為,妨害應當是對物權的圓滿狀態的影響,而不包括物權人自身受到的影響。問題在于,物權受到的影響和物權人受到的影響該如何區分?例如,鄰居家的圍墻太高,導致所有人難以得到充足的陽光。此時,所有人是否可以要求鄰居排除妨害?筆者認為,物權人所受到的影響只要與物權存在關聯性,就應當同時被理解為是物權也受到了影響,從而允許物權人行使排除妨害請求權。反之,如果二者之間不存在關聯性,則物權人不能行使該項權利。
4.排除妨害與恢復原狀的區分
排除妨害請求權是物權請求權的內容,而恢復原則是侵權損害賠償的內容,因此,如何區分二者是正確適用排除妨害請求權的重要問題。舉例而言,甲的大樹傾倒,砸在乙的房屋上。如果要求甲排除妨害,是要求其將大樹移開,還是要求其還要將乙的房屋修復。筆者認為,排除妨害請求權是針對特定的行為或狀態而言的,它要求消除影響他人物權圓滿性的行為或狀態,超出此限度的范圍就認定為恢復原狀。就前例而言,甲只負擔將其樹木移開,而不應當修復乙的房屋。如果乙要要求甲修復房屋,必須提起侵權損害賠償之訴。
5.排除妨害請求權與登記更正請求權
我國《物權法》第19條規定,在不動產登記簿記載的事項錯誤時,物權人享有的登記更正請求權。問題在于,登記更正請求權與排除妨害請求權的關系如何?筆者認為,登記錯誤應當理解為法律上的妨害,因此,真正的物權人可以請求登記記載的權利人排除此妨害,這也應當被理解為是排除妨害請求權的行使。
五、消除危險請求權
消除危險請求權,相當于國外民法上的妨害預防請求權,是指物權可能遭受侵奪占有以外的方式的妨害時,權利人享有的請求消除妨害可能性的權利。
(一)消除危險請求權的構成要件和效力
消除危險請求權的構成要件包括如下幾個:
其一,物權有受妨害的可能。例如,甲的一棵樹即將傾倒,乙的房屋有被砸壞的可能性,此時,可以請求消除危險。至于何為“妨害的可能”,對此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妨害一度發生”說。依照此種觀點,妨害一度現實發生且存在將來再產生妨害的可能,才能認定有“妨害的可能”。《德國民法典》就采此種模式。[26]此種規定是為了避免妨害預防請求權的范圍不當的擴大。[27]二是“社會一般觀念”說。按照此種觀點,妨害是否可能不必要求妨害曾經發生過,而應當就各種事實,依據社會一般觀念決定是否有“妨害的可能”。我國臺灣地區“民法”采此種觀點。[28]我國《物權法》并沒有要求“妨害一度發生”,因此,我們采的是“社會一般觀念”說。事實上,德國司法實踐也已經放棄了《德國民法典》的做法,因為如此規定過于僵化,難免不利于充分救濟物權人。[29]因此,妨害曾經發生過,只能作為認定妨害再次發生可能性的因素來考慮。
其二,可能發生的妨害具有違法性。與前面相同,此處的妨害必須具有違法性。只不過,此處所說的妨害的違法性,是指可能的妨害是違法的,而非現實的妨害是違法的。
其三,請求權主體是物權人。因為《物權法》并沒有限制此處的物權人類型,因此,凡是其物權的圓滿狀態有可能遭受妨害的物權人都可以行使該項權利。
如果具備上述要件,物權人就可以行使消除危險請求權。相對人包括可能的行為妨害人和可能的狀態妨害人,只要其對于可能的妨害具有支配力,有權消除可能的妨害,就是這里所說的相對人。
六、物權請求權行使的共通性問題
(一)物權請求權與訴訟時效
理論界對于物權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爭議頗大,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是肯定說,即認為,物權請求權應適用訴訟時效,理由在于:其一,它并非基本物權的一部分,而屬于獨立的請求權;其二,它適用訴訟時效,可以督促權利人盡快行使權利。[30]二是否定說,即認為物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理由在于:其一,它不是獨立的請求權,而是物權權能的一種,它不得脫離其基本物權而消滅;否則,將使物權成為有名無實之權利。其二,只要出現物的侵害,物權請求權就會不斷發生,它也無法因時效而消滅。[31]三是折中說。此種觀點或者認為,原物返還請求權不應當適用消滅時效,而排除妨害和消除危險請求權應當適用;或者認為,在登記的不動產之上產生的物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而在其他物之上產生的物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
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學界無法達成共識,因此,立法者最終決定不作規定。值得探討的是,《民法通則》的規定是否適用?根據《民法通則》第135條的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二年,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民法通則》實際上發揮著民法總則的功能,它應當可以普遍適用于所有民事領域。這就意味著,如果沒有充足的理由,就應當適用該條的規定。但筆者認為,考慮到物權請求權的特殊性,《民法通則》第135條的規定不應適用,具體來說:其一,原物返還請求權不能適用訴訟時效。如果原物返還請求權如果適用訴訟時效,將導致所有人雖享有所有權但無法請求返還的尷尬局面。其二,排除妨害請求權和消除危險請求權無法適用消滅時效。就物權而言,只要出現物的侵害,排除妨害請求權和消除危險請求權就會不斷發生,[32]二者適用訴訟時效也沒有實際意義。
(二)行使物權請求權的費用負擔
我國《物權法》并沒有明確物權請求權行使的費用負擔。理論上,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容忍請求權說。此種觀點認為,物權請求權以得否請求相對人為積極行為,可以分為積極請求權與容忍請求權。在容忍請求權的情形,僅權利人有請求相對人容忍其取回物、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險的權利,相對人當然不負擔其費用。而在積極請求權的情形,相對人應當負擔行使物權請求權的費用。至于積極請求權與容忍請求權的區分,一般認為以相對人有無過錯為標準。[33]二是共同負擔說。此種觀點認為,在相對人可歸責的情形,物權請求權行使的費用應由相對人負擔。但如果雙方當事人對于排除侵害的事由的發生均無可歸責原因時,則依據公平原則由雙方當事人平均負擔。[34]
筆者認為,容忍請求權說較為合理。如果相對人對于導致物權請求權發生的事由具有過錯時,由相對人負擔此種費用自屬合理。如果相對人沒有過錯,權利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權利的圓滿狀態而支付的費用,不應當隨意轉嫁給他人。
【作者簡介】
周友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注釋】
[1]另外,物權請求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物權請求權包括狹義的物權請求權和占有保護請求權。本文采狹義的物權請求權概念。參見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修訂版)(上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09。
[2]《物權法》第36條規定:“造成不動產或者動產毀損的,權利人可以請求修理、重作、更換或者恢復原狀。”
[3]參見曾世雄.損害賠償法原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4-5。
[4]參見侯利宏.論物上請求權制度[A],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5]參見韓世遠.合同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837-838。
[6]參見《物權法》第34條。
[7]參見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修訂版)(上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22。
[8]鄭玉波.民商法問題研究(三)[M],臺灣:1982年自版.71,72,84。
[9]參見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31-132。
[10]姚瑞光.民法物權論[M],臺灣:1988年自版.54-55。
[11]參見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修訂版)(上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19。
[12]參見鄭玉波.民商法問題研究(一)[M],臺灣:1991年自版.345。
[13]參見《城鄉規劃法》第64條。
[14]鄭玉波.民商法問題研究(三)[M],臺灣:1982年自版.72。
[15]參見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35。
[16]鄭玉波.民商法問題研究(三)[M],臺灣:1982年自版.71,72,84。
[17]姚瑞光.民法物權論[M],臺灣:1988年自版.56。
[18]王洪亮.物上請求權制度的理論繼受[J],中外法學,2006(1)。
[19]王洪亮.物上請求權制度的理論繼受[J],中外法學,2006(1)。
[20]BGHZ43,178ff.;24,21ff;Studien Komm/Jan Kropholler,§823,Rn.24.
[21]BGHZ24,21ff.
[22]Studien Komm/Jan Kropholler,§823,Rn.25,25,16,16.
[23]Studien Komm/Jan Kropholler,§823,Rn.25,25,16,16.
[24]Studien Komm/Jan Kropholler,§823,Rn.25,25,16,16.
[25]Studien Komm/Jan Kropholler,§823,Rn.25,25,16,16.
[26]參見史尚寬.物權法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66。
[27]參見鄭玉波.民法物權[M],臺北:三民書局,1995.64。
[28]參見鄭玉波.民法物權[M],臺北:三民書局,1995.64。
[29][德]鮑爾施.蒂爾納著,張雙根譯.德國物權法(上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41。
[30]參見洪遜欣.中國民法總則[M],臺灣:1992年自版.569。
[31][日]我妻榮.民法總則[M],東京:有斐閣,1988.378.轉引自梁慧星主編.中國物權法研究(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00。
[32][日]我妻榮.民法總則[M],東京:有斐閣,1988.378.轉引自梁慧星主編.中國物權法研究(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00。
[33]參見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31-132,135,139,140。
[34]參見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31-132,135,139,140。